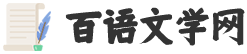當我們相互離開,我們也就離開了
那有著煙熏房舍的被冷落的郊區
我們在那里住了一個月,我們度過一夜的鎮子
忘了名字,還有那發出惡臭的亞洲旅店
以及那沿著從雅典到德爾斐的道路
當我們相互離開時我們也離開了它們。
山水隔人,把人連起來的,也是山水。
隔在河兩岸,此岸與彼岸,即使有橋可通,隔水相望,亦覺遙遠。隔在河兩端,比隔在河兩岸,更近還是更遠?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很喜歡這個句式,撲面而來的民歌風味。我與君對起,重疊復沓,詠嘆悵望。長江很長,一頭一尾,懸隔千里,難以逾越的空間距離。
“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不見而相連,因為共飲一江水;共飲一江水,卻思而不見。一體兩面,悲喜難言。還可以說,我們普照同一個太陽,共看同一個月亮,吹過我的風,也吹到你那里。
在更高的維度,從來就沒有分離,你我從來都在一起。然而,在這個維度,此身所在的時空點,即被我們認為所在的這里,你我相隔迢遞,根本不在彼此的世界里。
此水流不休,此恨無時已。隔在江水的兩端,就是隔在時間的兩端,這又平添了一層遙遠。一開始是空間距離,慢慢地,變成了時間距離。不知不覺中,你我已在不同的時空。
最后,只剩一個愿: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這句話聲音很輕,不大確定,幽幽吐出幾個字,目光落在未知處。你我的平行時空還會交叉嗎?還會重疊嗎?一切皆有可能,也就是說,一切皆有不可能。
不必認真,這只是一首流行歌曲,一首古老的情歌。歌詞俊美,有古樂府遺意,很適合彈著六弦琴,獨自坐在江邊輕輕地唱。江水靜靜流淌,直到我唱完我的歌。
所有的河都流向大海。每條河有自己的旅程,有自己流過的風景,有一個一個的渡口。人生也是一條河,每個人有自己的旅程和風景,有一站一站的愛情或友情。
汴水流,泗水流,這些發源于北方的河流,一路往東南流去,朝宗于海。海太遠了,看不見,也太茫然,看得見的是渡口。“流到瓜洲古渡頭”,渡頭是水陸交換的地方,是離去和到來的中轉站,古渡頭更有味道,像一位白發漁樵,看著一道道小水來到這里,匯入大河,再流向更遠的海上。
到了瓜洲古渡頭,便進入了吳地,便不再是北方的河流。詩中人的目光跟隨著汴水泗水,一直望向東南,心逐流水,過了渡口,風景為之一變。天末吳山點點,在離人眼中,皆化為愁。“點點”二字,畫出吳山之多、之青,以愁眼觀之,山秀變成山愁。
山是愁山,水便是恨水。“思悠悠,恨悠悠”,筆接流水,意入人情,思君如流水,恨君如流水,“悠悠”有一種無力感,愛恨交織,綿長無盡。除非那人回來,“恨到歸時方始休”,“休”字痛快!這不是死別,死別是徹底無望,若有恨,也只能此恨綿綿無絕期了;這是生離,只要人活著,就不能說沒有希望。
“月明人倚樓”,讀到末句,我們才看見前面望著流水的那雙愁眼,那些所思所恨,原是樓上這個人的:明月當空,她倚著欄桿,脈脈含情,像一幅剪影。也許她并沒有看見汴水泗水,更不可能看見瓜州渡口,而是樓前或有流水,月光下水聲淙淙,將她的相思帶往遠人所在的地方。
如果把人生或命運比作一條河,那么此身便是河上的一只小紙船。河與河會相遇,也會分離,紙船載著我們,飄蕩在流波的世上。
且不管元大是誰,這首詩里有我們每一個人。從題目切入,“初發揚子”,詩情即起于從揚子津離開之時。揚子津也是個古渡,在長江北岸,離瓜州不遠,由于泥沙沉積,至唐中期,瓜州與揚子津相連成為一個渡口。
離別是個過程,但必有一些時刻,你能清晰地聽見生命在某處斷裂,看見時間線轉換像鐵軌分開,比如火車的一聲鳴笛,車輪的一聲轉動,握緊的手松開或一個轉身,水行者棹舉、舟去。那一刻,你心里頓時離情洶涌。
然而,寫離情不可過于凄慘,越是強烈的情感,越不能任其宣泄,因為一旦落于語言文字,任何呼號對于聽覺都不很得體,可能還會適得其反。洶涌過后,在涼風吹拂的寂靜中開始下筆,愈克制含蓄,愈見真心。韋應物這首詩便淺淺說出,筆意至淡,情卻至深,細詠回味不盡。
“凄凄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凄凄”一詞,在整首詩中最重,是乍別時的心情。“親愛”這個詞,今人很熟悉乃至被用濫,不禁莞爾,唐代詩人之間的情誼,恐非我輩所能望及。
“泛泛”有搖晃感,人在舟中,隨波上下,失去了腳踏實地的穩定。江上煙霧迷茫,又令人失去方向感。這是登船乍離的感受,其實對于我們也并不陌生,當我們下樓,走上川流不息的大街,也會有一瞬的茫然,自我身份忽然變得模糊。
這也不只是城市里才有的漂浮感,小時候村西有一條大路,就叫西大路。不知是否太寬的緣故,不知是否有大汽車的緣故,一走上西大路我就頭暈,就覺得心中空茫。和村子周圍別的路不一樣,別的路都是回家的路,西大路通往縣城,通往火車站,是離開的路,我就是從那條路上一去不返。
“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這兩句寫得平淡,卻傷我心,一地之于另一地,是多么虛幻。歸棹去往洛陽,我將是洛陽人,廣陵已在視線里消失,如水在身后合攏,殘鐘余韻,回蕩于煙樹朦朧的天際。
離別,就是死去一點點,是對往昔所愛的一種死去,也是完成了一個輪回。“今朝此為別,何處還相遇?”也許再不會相遇,縱然再相遇,也將不再是今朝的彼此。“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人因世事漂流轉徙,世事是波流,人是波上舟。風在流動,水在流動,生命也在流動,不論順流還是逆流,船都會行走。
連用兩個問號,表示未知,也表示反問。你我都是河上的紙船,匆匆相遇,又匆匆別離,往往來不及留下一個美好回憶,哪里還容得下互相怨恨互相敵對。
說到長江水,想起明代楊慎的《臨江仙》,這首詞本是為《廿一史彈詞》第三段《說秦漢》而作,后被明末清初毛宗崗父子拿去置于毛改本《三國演義》的開篇,也因此而廣為人知。
國人喜歡談古論今,即使鄉村野叟,夏夜納涼,坐在月下,也會搖著蒲扇說起秦漢三國,臧否歷史人物,以近于癡的天真,隨興說夢,語之鑿鑿,仿佛親歷親聞,仿佛月亮可以作證。
在歷史的長河中,英雄就是那幾朵浪花,河水滾滾流淌,浪花轉瞬淘盡。是非成敗轉頭空,每個人向外追求的一切,莫不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長江,青山,夕陽,不是人類舞臺上的背景,相反,一代代人只不過短暫經過了它們的夢。
白發漁樵也是楊慎的寫照,因言獲罪的他被謫戍流放,老死于滇南邊陲,自身際遇與歷史興亡,使他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這真是個等閑曠達的態度。離世界距離越遠,越邊緣,越能看出其荒誕;離歷史距離越遠,越超然,越能將往事付諸笑談。
但我卻不能如此輕松,也很怕讀史書。讀史未必使人明智,倒是使人心情沉重,讀著讀著便要拍案而起、廢書而嘆。都說以史為鑒,不重蹈歷史的覆轍,然而同樣的覆轍一蹈再蹈。如果世界是一個夢境,固然萬事不必當真,可是夢里會恐懼會疼痛,所以還是希望都能做美夢,而不是噩夢連連,更不要在同樣的噩夢里反復循環。
一江水是什么?是古今,也是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