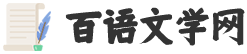2022年1月8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會議室,經過14位評委的充分討論與評審,2021年收獲文學榜最終榜單揭曉。
2.《輪到我的時候我該說什么》陳沖
5.《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楊瀟
4.《我父親的奇想之屋》韓松落
余華講述了清末民初動蕩年代里,北方青年林祥福與南方女子紀小美之間的命運與際遇。蒼茫亂世中的江湖義氣、男女恩情是小說的素樸質地,慈悲之情浸潤在作品的字里行間。母子、父女、母女、夫妻、情人、主仆、萍水相逢之人之間,都有一種難以命名的情義……這是一次“有情”召喚,它召喚的是我們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民間之情,是生發于我們民族傳統內部的仁義與德行。余華寫出了綿遠、悠長、蒼茫的命運感,寫出了鮮血亂離世界的恒長。那些看似無情實則柔情百結、既隱忍又剛勁、既卑微又高貴的生存樣態雜糅在小說內部,形成了獨屬于余華的五味相陳、有情有義的小說調性,是屬于我們時代優秀小說家的“持續的成熟”之作。
作為當代文學的新面孔,林棹有豐沛的想象和精微敏銳的觸覺。她以元氣充沛、恣肆汪洋的語言,為我們創造了名為“虛構之物”的雌性巨蛙。隨著巨蛙的出現,一場語言盛筵由此開啟,既真實又奇幻的世界蜂擁而來,讀者情不自禁被裹挾、牽引,共赴新鮮而陌生的地域之旅、語言之旅、奇跡之旅。文學想象的邊界在小說中被一次次拓展,小說家“巨蛙”般獨屬于女性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令人贊嘆。《潮汐圖》里有著顛覆尋常文學審美的、獨屬于小說家林棹的創造力和美學氣質,是2021年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驚喜收獲。
從《一個人的戰爭》到《北流》,借助于南方方言的征用、“注疏”式文體的設定,林白從個體化的存在,到中國人的存在,最后抵達人類的存在;從地方性的寫作,最終抵達世界性的寫作。作家徹底打開了自己,打開了生活,打開了世界,打開了人類的存在。
在一部明顯借鑒了推理小說藝術元素的長篇小說中,既能夠對人物形象展開深度的精神分析,也能夠相對充分地表達作家的社會關懷,《回響》所呈現的思想藝術價值,理當得到我們的肯定與認可。
小說有著堅硬的精神厚度,以一樁兒童失蹤案開啟敘事,接續了現實主義關懷的寫作傳統,恢復了平凡生活中的英雄視角,將主題敘事與文學追求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勾連起歷史與當下生活,寫出了寧靜生活下的波瀾壯闊,展現了小說家既沉入現實又超拔向上的意識和能力。
摭拾故實、采編舊聞,以特定地理的折沖樽俎將史書的零散記載貫通一氣,以通達曉暢的筆法重新講述了中間地帶的毆脫敘事,歷史認識與判斷同文學表達與啟示有機交融在一起,將定居文明與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編織為整全的中國文化圖景,恢復了有情有識的文史書寫傳統。
2.《輪到我的時候我該說什么》陳沖
為讀者展現了一個文學意義上獨特又深沉的陳沖,她以克制內斂的筆法向著家族歷史征進,踏進如煙的家族往事又不沉溺其中,通過眾多日常的生活細節完成了對家人形象的刻寫和賦形,從而與歷史生活達成了深沉又動人的聯系,作品呈現出的沉郁悲憫讓人為之動容。
從親歷體驗與自我療救出發,細致勾勒出抑郁患者的生理與心理行狀,兼及精神病醫學的知識普及和歷史脈絡梳理,點面結合,描述與分析并重,既有切膚的痛感,亦有超出一己的關切,從社會認知與撫慰的角度顯示出文學的多重價值功能。
在歷史轉折的大背景中,敘述了新中國成立前夕民主人士從香港北上,參與籌建新政協、創立新中國的壯舉,呈現了一段隱秘而偉大的歷史。作者宏觀著眼,微觀落筆,結構紛紜復雜的歷史,抒寫歷史中的世道人心。字里行間風云變幻,滄海桑田,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光明大道上跋涉的人物群像躍然紙上,可歌可泣。
5.《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楊瀟
真正的非虛構寫作是“行動”,是將思索付之行動,是將行動凝聚為文字。對于寫作者楊瀟而言,“重走”的意義便是行動,作家從長沙到昆明,重走了1600公里聯大西遷路;與此同時,“重走”也是一次紙上追蹤,是在時間意義上回溯過往,是從歷史觀照當下。切實、充實、發人深省、引人深思,不僅記下了歷史中的行走,也寫下了今日青年對于歷史的致敬與思考。楊瀟的寫作拓展了非虛構寫作的邊界和維度,他以自己的行動為當代文學貢獻了非虛構寫作的另一種范本、另一種路徑、另一種可能。
北京、縣城和陽關山上之空間騰挪和想象亦是中國現實圖景。小說直追鮮卑匈奴之古中國貴族、隱士與流民的山林前史、流脈和精神殘余,為搬遷、聚居和游徙縣城的山民辯護。游小虎、游小龍和“我”都是生命的遠征者和潰敗者,他們的想象和止步,恰恰是今天中國社會階層想象和止步的具體而微的樣本。“以鳥獸之名”,是游小龍的日常文學書寫,也是他叩問生命來處的漫長修行。緣此,藏身滾滾紅塵的當代隱者得以安妥細小生命。因為游小龍這個小說人物,小說可以視作孫頻獻給北方縣城故土和故土文化、精神血脈頑強賡續者的一曲挽歌。孫頻是不斷追求個體文學革新的年輕小說家,她不為既有虛名所困累,幾乎每一部新作都成為一個新的起點。小說在自然、歷史和當代諸維度上重新定義“山林”之于個人精神成長的意義,敘述者“我”從縣城殺人事件的窺看者到融入山民生命日常的過程,亦即生命個體返觀自身的啟蒙之路。
黃立宇是一位久違的作家,《制琴師》揮灑出一股有別于主流文壇趣味的勃勃生機。一座城,兩三人,幾段旁逸斜出的軼事,編織了一出羅曼蒂克消亡史。那是文學靈韻的回響,是追念還未被整飭得齊整單調的華彩時代,也是致敬沉郁、堅韌卻歷久彌新的文學技藝。
小說中的戚老師,是奔月女神,是不忠的妻子,是不負責任的母親,小說在這三種沖突角色中展開;當死亡降臨,戚老師完成了所有做人的角色,她是完美的妻子,完美的母親,完美的女神。艾偉因此也完成了當代文學中,一位極其豐富復雜讓人不能忘懷的女性形象。
4.《我父親的奇想之屋》韓松落
一位不老的父親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出現,他出現的目的是為了消失——他總是在某一時刻突然無影無蹤,當然,他一定在消失前帶著孩子去看一處神秘的空間:樓中之樓,巨大發光的體育館,藏在山體里的飛機場……這是韓松落中篇《我父親的奇想之屋》的故事設置。這篇小說是一段少年的奇幻之旅,是卡爾維諾和博爾赫斯式想象的吉光片羽。它以“同時性”的敘述顛覆了現代性的一元論時間觀。這是本年度讓我驚艷的作品之一。
呈現了漢語敘事的魅力和可能達到的美,作者對一草一木,對人,對世道人心,都極其敏感。人性中,有懷疑,有欺騙,有深不可測的陰影,但是在作者慈悲的目光下,都放下了,天心月圓,悲欣交集。這是一部見性成佛的小說,不僅是作品中的人物,對作者和讀者,也是如此。
活畫了校園小世界里的新景觀。兩位博士太太周太太和朱太太,一個是《圍城》里的蘇文紈,一個是《聊齋》里的聶小倩。在彼此莫名的敵意和相互羨慕里無休止纏斗,用校園家屬樓金輝小苑與圖書館古籍部作竹林,以周太太留學歸國的兒子達利當暗器,閃展騰挪,上下翻飛,往返投擲,樂此不疲。最終以朱太太聶倩成功降服達利而告勝出。白琳以冷靜無情的筆觸宣告了傳統面對現代的失敗,母性面對女性的失敗。
無論書寫怎樣的情景,王凱都仿佛天然地免于一本正經,處處有著輕微的諧謔調性,不緊不慢地呈現著人心暗處的卑微和無助,卻又因為對卑微和無助的認知與反省,掘發出人性更深處某些干凈明亮的地方,從黑夜中傳遞出些微澄澈的星光,為人贏回了一點踏實的尊嚴。
憑借出色的想象力和嚴密的邏輯力,李宏偉構想了一個飽滿的未來社會,用虛構中的試驗來檢視人類現實和思維的某些界限,并以復雜的人物形象來嘗試打破這些界限的可能,其中隱含著人或未來的某種成長契機,從而啟發人們更為雄沉地面對現實世界。
優秀的作家往往都會抓住能夠使小說誕生的某種靈感,這種靈感就會帶著妙趣橫生的文學基因,賦予小說健康生長的諸多可能性。《仰頭一看》就是這樣一篇得天獨厚的作品,四個字讀完的一瞬間所決定的人生命運讓人覺得匪夷所思,小說的主人公還能否在陰影籠罩下把握住自己的人生困境?在特別容易歧路亡羊的小說道路中,《仰頭一看》在呈現出小說家循著直覺而產生的非凡魅力的同時,也使那些只依賴匠氣制作的小說黯然失色。
故事雖然置放于近未來的日本,但科幻和異域的設定背后所探索的是當下人心領神會的社會癥結,尤其是知識分子因戰爭的黑暗記憶而深深苦惱并全力肉搏的存在主義大哉問:何為個體的真實,何為自由的生命,何為存在的根基。年輕世代的華語寫作者向了不起的一代知識分子精神致敬,縱使時空間隔,文學依舊能將美好和深邃的心靈并聯在一起,成為照亮黑暗燧道的炬火。
我們朝夕在焉卻能坦然隱然在焉,分裂的日常生活被鐘求是《地上的天空》誠懇地敞開。小說“小”事,“我”給離世的友人朱一圍處理藏書,從他地上光明的生活通向其隱秘的地下生活。悖謬的是一直作為我們地上生活想象異邦的天空,只能被朱一圍和陳宛小心移放到地下(來世)生活。故而,所謂地上的天空,只是天空在大地的倒影。如果筱蓓、陳宛和朱一圍——他們都是如我們大多數人一樣的無辜者和無名者,都承擔著命定地上生活的局囿;與此同時,我們頭頂的天空存在著,也是我們想象合理和必須的到達,那么,朱一圍的一“圍”之脫困,從地上走向天空的路在哪里?小說的答案之處恰恰是提問之處。《地上的天空》作為短篇小說的魅力,在于它是經由狹小的切口而曲其微而幽其深地洞開,進而在不可能處開鑿可能的審美秘徑。
似乎有意恪守著某種屬人的局限,趙松從不輕易拉下情節的布幔,而是始終保持著敘事的克制,耐心追摹著每個細節可能的完整因果,人物也在綿密的日常中一點點透露出自己的隱秘心思,從而能夠讓我們覺察到人性深處那些微妙的皺褶、潛藏的欲望、深埋的悲歡。
鐵凝的《信使》是愛與罰的深情故事,也是啟蒙與救贖的人間童話。作家以一貫溫潤與明朗的筆觸,塑造了美麗的“信使”李花開的形象——她就是鐵凝作品里曾出現的農村女孩香雪、紅衣少女安然、《玫瑰門》里的小蘇眉、《永遠有多遠》里的白大省。她們一路走來,初心不改,帶著梨花的芬芳和鐵皮石斛的剛烈,長成了《信使》里的李花開。李花開得知真相后從房頂上的縱身一跳,是信義與道義的騏驥一躍,也是步入經典女性人物形象長廊的精彩一搏。
兩個殘缺的人相遇了,他們小心翼翼地在彼此的殘缺里尋找一種圓滿的可能。他們彼此試探、摸索、有限度地觸碰,他們進入得越深,就發現傷痕和黑暗越多,生活簡直就是一場接一場的悲劇。青春文藝劇和港臺警匪劇里的元素在這里幾乎都出現了,且快速地推進,這使得作品在某些關鍵點上的停留不夠久,而夢境的頻繁使用也讓故事的邏輯顯得不那么堅實。不管如何,葉昕昀的《孔雀》依然值得推薦,她是一位新作者,卻有著成熟作家才能具有的個人風格的鮮明。
一個不幸的母親生了兩個兒子,一位接受現代教育,成為了一名小有名氣的醫生;一位則是活佛轉世靈童,被送進了寺廟。小說試圖在傳統與現代,信仰和理性之間找到一種和解——最后這兄弟倆彼此似乎理解了對方,但這種理解并非是認同,而是對生命無常的恐懼和敬畏。萬瑪才旦的敘述干凈、簡潔、節制,是對當代寫作過于“修飾性”的一種反撥。
未知生,焉知死?小說卻以死亡降臨于死者與生者的點點滴滴過程,來反復辨識死亡之于價值的確認。在董夏青青的敘述中,人們感到需要成全一種比現在更美好的生活、更莊嚴的人性;更重要的是,相信人們有能力爭取上述二者的實現。這是至難的目標。因為在經歷了現代主義文學的洗禮之后,攜帶著價值意涵的敘事,必須從教條化的道德訴求與空洞化的人格符號中選擇出自身,文學敘事必須彌合“可愛”與“可信”之間的裂隙。董夏青青迄今幾乎所有的創作,都處于向上述至難目標的跋涉途中,就此我們也見證了一位青年作家的信仰、耐心與文學技藝。
《晚春》是三三以人之子而不是龐然的一代人寫給父輩的理解之書。從父輩的1972到“我”和父輩的2021,一個中國普通家庭半個世紀的長史被“短篇”收納。作者“三三”和三三本名的真身都隱身敘述者“我”之“他”,從而為自由表達贏得空間,那些年輕一代寫作的文學資源、時代記憶和個人經驗得以釋放,包括三三個人的可能和局限。被時代吸附,或者被時代拋出,俗世兒女們最終面對的只是一己之身的世界,且如此之小世界,對于單個的人也可能是未知的、晦暗不明的、危機四伏的,故而一切小兒女的哀痛、憂懼、孤獨、念念不忘以及生而為人的進退失據在《晚春》皆見之于敘事的節奏和語言的發微。
熟悉文學江湖的中國當代文學讀者,自然也可能熟悉每一個江湖有其聲名的寫作者所屬的文學綱目。不同的文學綱目,自有其經得起溯源的路線圖。所以《跳馬》的抗日故事、鄉村權力生態和鄉民日常等的勾描,不是路內的小說,不是我們熟悉的“十七歲的輕騎兵”和“霧行者”。《跳馬》中,昔是體育教員和讀書郎,現為抗日隊伍正副大隊長的兩人,他們未來中國的想象著陸在訓練一個父母雙亡無羈的小孩學習“跳馬”。逃亡途中小孩騰身一躍的起跳和完成,放在小說設定的歷史時間內,寓現實的沉痛和想象的飛動,正是我們熟悉的路內小說灌注的神氣。
當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所有人都只剩了半張臉,自我就消失了,故事就開始了。小說捕捉到了當下的普遍特征,半張臉,是具象的,也是形而上的,是時代的準確隱喻。
《喝湯的聲音》是一篇非常獨特的小說,小說關涉久遠慘烈的那段歷史,它一直影響著幾代人的命運。痛苦的記憶不是停留在宏大的敘事之中,而是滲透并循環在人的血液里。遲子建通過一個夢魘所生發出來的故事,使那些被遺忘的傷疤通過最日常的方式喚醒人們麻木的神經,也使小說的蘊涵轉化為永遠響徹云霄的一種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