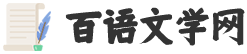【建安別裁】夢也無聲:《七哀詩》之五――樂府詩的文人化【終篇】
在文學初起的《詩經(jīng)》時代,人們沒有太多的閑情,歌是用來勞作時助力,閑暇時詠唱抒懷的,所謂“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雖然風格各異,但文壇上――如果有這么一個文壇的話――并不存在思想立場的分歧。
隨著物質(zhì)文化的進步,尤其是社會上產(chǎn)生了專門的文人階層,他們不用勞作,因而有更多的閑情來推敲文字,文學也就越來越傾向于一種奢侈品,很多文人屈身于俳優(yōu)地位,專門侍奉王室貴族,文學也傾向于華麗鋪張,風格漸漸軟糜,賣弄粉飾,使得文字更加艱深,脫離社會生活,使得內(nèi)容空洞繁雜,感情游離不實,使得文學漸次背離了表情達意的本尊。現(xiàn)實主義的傳統(tǒng)只在民歌中傳承,但民歌的角色和社會地位尚不足以爭衡文壇。
一些有識見有抱負有才華有勇氣的正直文人,開始反其道而行,努力恢復文學獨立于勢力和娛樂之外的尊嚴感,回到國風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傳統(tǒng),這樣,在漢末建安時期,比較明顯地產(chǎn)生了兩種文學思想文學實踐的分歧。
以曹操為首的建安詩人在漢末離亂中重新舉起樂府民歌的大旗,用“端直的言辭結(jié)合駿爽的意氣,形成格調(diào)勁健和藝術感染力很強的"風骨”,直接針對空洞富麗的“上流文學”,把焦點聚光在社會生活中,把民間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的文學傳統(tǒng)發(fā)揚光大,寫離亂,寫世情,寫苦難,寫抱負,為生民立命,為天下立心,把一有機會就忍不住向富貴華麗雍容閑散“投懷送抱”的幫閑傾向拉回到《詩經(jīng)~國風》留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中。
樂府敘事詩的文人化過程,表現(xiàn)最突出的是王粲的《七哀詩》,《七哀詩》的主體與樂府民歌敘事詩同出一轍,此前的樂府敘事詩,像《十五從軍征》、《婦病行》等,以場景、對話、動作、表情為主要元素,構(gòu)建一個框架,白描一個完整的情節(jié)或者故事,他的目的是講述一個故事,僅此而已。
而所謂的文人化傾向,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語言文字更加洗煉有高度的概括性,這種概括性本身多少傷害了故事情節(jié)的生動性直觀性,比如王粲寫母親“抱子棄草間”,五字之間表現(xiàn)了幾個動作,而《婦病行》開頭,“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則顯得繁復而具體,因之故事性也更強。
另一個方面,文人化傾向還體現(xiàn)在主觀投射上,這是比之練字造語更主要的特征。
在敘述故事的過程中,用精準簡練的文字,除了描述動作語言,還帶著明確的詩人自己的主觀感受,就母親的動作本身來說,不存在“棄”的問題,客觀地說,王粲所見只是“抱子放草間”的動作,但他不說“放”而直言“棄”,就已經(jīng)離開了故事的本色而戴上了“有色眼鏡”,“棄”是王粲從觀察中得出的結(jié)論,把結(jié)論和情節(jié)放在一起說,就不再是客觀單純的故事,而成了詩人“講給讀者的故事”。
“不知淚下一何翩翩”也是抒發(fā)感受,但這感受的傳達是靠了動作本身造成的聯(lián)想實現(xiàn)的,“翩翩”只是帶著感情色彩的詞,而不帶著理性的評斷。這就是二者的區(qū)別。
《婦病行》講了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作者并不出現(xiàn),讀者對故事的感受,完全從故事的敘述中自己梳理出來,可以是同情、不忍或者其他,作者沒有強加于讀者的定向感受。
而《七哀詩》寫那個“抱子棄草間”的故事,主旨是寫詩人看到這個情節(jié)之后,思想立場和感受都起了明顯的變化,出發(fā)點在詩人本身,主線是記錄詩人的行程、經(jīng)歷和感受,故事只是它的副產(chǎn)品,詩人強調(diào)的是他對這個故事的感受,故事本體是附著于詩人的感受之上的,讀者只能圍繞著王粲“驅(qū)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的感受,或共鳴或反對。
后來的《西洲曲》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的描繪,《木蘭辭》中,“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發(fā)揮,除了句式整飭精煉外,更主要是這一類帶入的主觀傾向,偏離了樂府民歌的基本風格形式,而有了文人詩的本質(zhì)特征。
在《小樓聽雨詩刊》公眾號發(fā)布的作品,同時會在【百度】【今日頭條】【華人號】【都市頭條】【搜狐網(wǎng)】【鳳凰新聞網(wǎng)】【UC瀏覽器】【天天快報】【騰訊新聞】【QQ瀏覽器】【QQ看點】【360圖書館】等主流平臺網(wǎng)頁版同步刊出。敬請作者自行關注并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