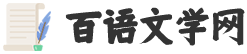在唐高宗顯慶四年(659),一名男嬰呱呱落地,從此一顆新星冉冉升起。陳子昂出生在梓州射洪(今屬于四川省),家中富庶安康,從小就養成了豪家子弟任俠使氣的性情。青年時期,他幡然醒悟,開始折節讀書,21歲時進入長安游太學,第二年奔赴洛陽應試,不幸名落孫山,心灰意冷,于是就在家鄉度過了兩年的隱居生活。
永淳元年(682),年僅23歲的他,再次應試,得中進士,從此進入仕途。陳子昂性格耿直,敢于直諫,因兩次上諫,受到了武則天的賞識,被提拔為秘書省正字,官拜右拾遺。
成就一番功業,留名青史是陳子昂事業的終極追求,所以他毅然從軍邊塞,跟隨喬知之北征,躍馬荒漠。之后又跟隨武攸宜出征契丹,但因直諫被降職,憤而辭職還鄉。還鄉后,他被縣令誣陷入獄,在久視元年(700)永辭人世。
陳子昂一生雖短暫跌宕,但卻是振興一代詩風的關鍵人物。他的詩歌中沒有初唐詩歌的矯揉造作,纖巧綺靡,而是提倡風骨,注重詩歌的現實精神。他的三十八首《感遇》詩就體現了他的詩歌思想,既有為時為事為政而作,也有抒發俠肝義膽的抒懷言志之作。
他的“骨氣端詳,音情頓挫,光英朗練”的詩美理想,將壯大的情思與聲律和詞采的美相結合,創造出健康瑰麗的文學,影響了有唐一代。
在陳子昂的眾多詩歌中,家喻戶曉的便是他的登臺之作《登幽州臺歌》。
這首詩作于武則天神功元年(697)年,陳子昂跟隨安郡王武攸宜北征契丹,軍次漁陽。但武攸宜性格輕率,缺少謀略,次年軍敗,陳子昂獻計納策,未被采取,反被降為軍曹。壯志難酬,命運不濟,他心中頓生苦澀惆悵之感,因此登上了幽州臺,慷慨悲歌,寫下了這首千古絕唱《登幽州臺歌》。
“往前不見招攬賢才的古代圣君,向后不見求才若渴的后世明君。只有蒼茫天地悠悠無限,我獨自熱淚紛紛,悲傷滿懷。”
“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首詩前三句徑寫時空,最后一句直抒胸臆。我們雖未必知其事,曉其意,但仍舊可以在時空與個人的對比中感受到詩人的孤獨與落寞。
在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音義》引《尸子》中寫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前兩句是時間意義上的宙,悠悠天地是空間上的宇。這里的“古人”指的是古代能夠禮待下士的賢君明主。與《登幽州臺歌》同時而作的《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可以佐證,這組詩中對戰國時期燕昭王禮待樂毅、郭槐,燕太子丹善待田光等歷史事跡,給予了贊美,表達出作者對盛世的向往,對古賢豐功偉績的渴慕。
可是時間飛逝,歷史經歷了幾番的滄桑變化,那些像燕昭王一樣的伯樂已經化為了塵土,后來的賢主也來不及見到,自己滿腹的才華無人賞識,一腔報效祖國的熱血終究還是被時代辜負。
身處在悠悠的宇宙之中,自己愈發的渺小輕微,感受到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蒼茫之意,緊接著一種迎面撲來的孤獨感,將其包圍,無法掙脫。而這種時空給予的孤獨感無人分擔,只能獨自承受,數十年郁結在心頭的委屈與不甘便噴涌而出,熱淚滾滾,不能自已。
孤單落寞是古代大多數懷才不遇的讀書人所共有的獨特的人生體驗和生命意識,因而可以超越時空獲得廣泛的共鳴。
這首詩在用語造辭方面也頗有特色。它采用楚辭那種長短不齊的句式,不講究對仗的形式,音節錯落有致,行云流水,短短22個字,視野開闊,意境雄渾,明朗剛健,絲毫不受魏晉南北朝四六文駢儷形式的束縛,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明代楊慎在《升庵詩話》中評價:“其辭簡質,有漢魏之風。”
總而言之,這首詩歌,在天地悠悠與人生短暫的哀歌之中,充斥著不可一世的孤傲之氣,聚集成反差強烈的情感跳躍。無窮無盡的天地,將與英雄豪杰的不朽功業長存;反觀自己有限的人生,一腔報國熱血無處揮灑,只能長長嘆息,空留遺恨,于是乎悲從心中噴涌而出,匯聚成愴然涕下的巨大悲哀。而在這一己的悲哀之中,浸潤著得風氣之先的孤獨感,透露出英雄無用武之地,拔劍四顧茫茫而慷慨悲歌的豪邁氣概。
題目中的幽州是古代的十二州之一,也就是現今的北京市。幽州臺即薊北樓,又稱為燕臺,黃金臺。這個樓臺寫進了許多詩歌之中,成為了尊賢引才的象征,蘊含著無數懷才不遇,渴求伯樂的有志者心中的向往。那么,詩歌中的“黃金臺”的典故出自哪里?黃金臺又位于何處?我們接下來簡要地探討一二。
在《戰國策 ? 燕策一》中記錄了這樣一段史事: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仇。故往見郭隗先生……于是昭王為隗筑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吊死問生,與百姓同甘共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
燕昭王在公元前311年即位,收拾完燕國的殘局后,降低身份,計劃用豐厚的財物來招攬賢才,報仇雪恨,因而去拜見了郭隗先生。郭隗用“千金買死馬”的故事,再次勸導燕昭王用重金來求才,表明誠心。于是昭王尊郭隗為師,并為其筑宮臺。之后各路人才紛紛涌進燕國,燕國得以強大,最后燕昭王大仇得報。
這個典故在東漢文學家孔融的《論盛孝章書》也出現過,并首次提出了“燕昭王筑臺,以尊郭隗”的說法。
黃金臺位于何處,在學術界中有爭議。最終認為其在河北易縣東南,北易水南,也就是河北定興縣高里鄉北章臺上的可能性極大。
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在《易水》章節有對黃金臺的描述:“易水出涿郡故安縣(今易縣)閻鄉西山……易水又東徑武陽城南……易水又東與濡水合……其水之故瀆南出,屈而東轉,又分為二瀆。一水徑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其一水東出注金臺陂……陂東西六、七里,南北五里,側陂西北有釣臺,高丈余,方可四十步。陂北十余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加減,北有小金臺,臺北有蘭馬臺,并悉高數丈……”
隋朝的《上谷郡圖經》載:“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以上兩部著作比較早記載了黃金臺位置。
北宋《太平寰宇記》也記載過黃金臺的位置:“黃金臺在易縣東南三十里。燕昭王所造,置金于上以招賢士,又有西金臺,俗呼此為東金臺……”而易縣東南三十里就是在易水河附近,再次佐證了黃金臺在易水河附近。
明代蔣一葵的《長安客話》中記載:“黃金臺有二,古燕昭王所為樂、郭筑而禮之者,其勝跡皆在定興。今都城亦有二,是后人所筑。”由此可知,黃金臺在易水河和燕下都附近
因為燕下都(戰國時期燕國都城)都城在易水河畔,是燕國的軍事重心,心懷大志的燕昭王以此為霸業根基來重振燕國,那么,修筑黃金臺招賢也會在燕下都附近。另外爭論的一處北京城東南黃金臺,不過其不在易水河流域,自然可以排除在外。